注:《中国法理学发达史论》系梁启超研究中国法理学发展史的一部专著,收录于《饮冰室合集》第二卷中。全书包括绪论、法之起因、法之语源,旧学派关于法的观念,法治主义之发生等部分,另有《论中国成文法编制之沿革得失》作为附录,后因附录过长,将其独立成篇。从内容上看,主要论述了下列问题:(1)法理学存在的必要性:世界上有四大法系,中国是其中之一,有法系必然要有法理学。(2)法律与法理学产生的先后问题,以法律起源的观点看,因为大部分法律都是由习惯而来,经国家认可才能发生效力,因此,法理学产生早于法律,而以法律解释派的观点看,法理学则是由后人解释法律条文而产生的,法律又早于法理学而产生。(3)研究中国法理学、不应以法律解释学为主,而应以研究抽象的法理为主。(4)就世界范围而言,法国拿破仑法典公布后,法理学发展到全盛时期,就中国法理学发展来说,春秋时期达到全盛。(5)详细探讨了法、刑、律、典、式、范等概念的内涵。(6)综合儒家、墨家、法家的观点,研究了中国法的起因,探讨了儒、墨、道关于法的观念。(7)从法治主义与放任主义,法治主义与人治主义,法治主义与礼治主义,法治主义与执治主义的比较研究中,阐发了法治主义发生的原因,内容,历史作用。认为中国法理学完全发达,始于法家,但法家只能救一时之弊,因此,中国法理学很快由盛及衰,当今为中国法学革新之大好时代,必须深察中国民心,采集西人之长,惟适是求,大兴研究法理之风,复兴中国法理学。
绪 论
近世法学者称世界四法系,而吾国与居一焉。其余诸法系,或发生蚤于我,而久已中绝:或今方盛行,而导源甚近。然则我之法系,其最足以自豪于世界也。夫深山大泽,龙蛇生焉,我以数万万神圣之国民,建数千年绵延之帝国,其能有独立伟大之法系,宜也。然人有恒言,学说者事实之母也。既有法系,则必有法理以为之原。故研究我国之法理学,非徒我国学者所当有事,抑亦全世界学者所当有事也。
法律先于法理耶?抑法理先于法律耶?此不易决之问题也。以近世学者之所说,则法律者,发达的而非创造的也。盖法律之大部分,皆积惯习而来,经国家之承认,而遂有法律之效力。而惯习固非一一焉能悉有理由者也。谓必有理而始有法,则法之能存者寡矣。故近世解释派(专解释法文者谓之解释派)盛行,其极端说,至有谓法文外无法理者,法理实由后人解剖法文而发生云尔。虽然,此说也,施诸成文法大备之国,犹或可以存立,然固已稍沮法律之进步。若夫在诸法樊然淆乱之国,而欲助长立法事业,则非求法理于法文以外,而法学之效用将穷。故居今日之中国而治法学,则抽象的法理其最要也。
我国自三代以来,纯以礼治为尚。及春秋战国之间,社会之变迁极剧烈,然后法治思想乃始萌芽。法治主义者,应于时势之需要,而与旧主义宣战者也。夫礼治与法治,其手段固沟然不同,若其设为若干条件以规律一般人之行为,则一也。而凡持旧主义者,又率皆崇信“自然法”(说详第四章)。其所设条件,殆莫不有其理由,其理由之真不真适不适且勿论,要之谓非一种之法理焉不得也。而新主义之与彼对峙者,又别有其理由。而旗帜甚新,壁垒甚坚者也。故我国当春秋战国间,法理学之发达,臻于全盛。以欧洲十七世纪间之学说视我,其轩轾良未易言也。
顾欧洲有十七八世纪之学说,而产出十九世纪之事实。自拿破仑法典成立,而私法开一新纪元;自各国宪法公布,而公法开一新纪元。逮于今日,而法学之盛,为有史以来所未有。而我中国,当春秋战国间,虽学说如林,不移时辄已销熄。后此退化复退化,驯至今日,而固有之法系,几成僵石。则又何也?礼治主义与夫其他各主义(如放任主义、人治主义等),久已深入人心,而群与法治主义为敌。法治主义虽一时偶占势力,摧灭封建制度、阶级制度(战国秦汉之交,吾国固有之封建制度、阶级制度一时摧灭。虽儒法两家并有力,而法家功尤伟。说详第六章)。然以吾国崇古念重,法治主义之学说,终为礼治主义之学说所征服。门户之见,恶及储胥,并其精粹之义而悉吐蔑之。而一切法律上事业,悉委诸刀笔之吏。学士大夫,莫肯从事。此其所以不能发达者一也。又法家言,主张团体自身利益过甚,遂至蔑视团体员利益。虽能救一时之敝,而于助长社会发达,非可久适。其道不惬于人心,虽靡旧说之反对,势固将敝。而儒墨家言,又主张团体员利益过甚,于国家强制组织之性质,不甚措意。故其制裁力有所穷,适于为社会的而不适于为国家的。夫以两派各有缺点,专任焉俱不足以成久治。而相轻相轧,不能调和,此其所以不能发达者二也。坐此二弊,故虽于一时代百数十年间,有如火如荼之学说,而遂不足以开万世之利,造一国之福也。
逮于今日,万国比邻,物竞逾剧,非于内部有整齐严肃之治,万不能壹其力以对外。法治主义,为今日救时惟一之主义。立法事业,为今日存国最急之事业。稍有识者,皆能知之。而东西各国之成绩,其刺戟我思想供给我智识者,又不一而足。自今以往,实我国法系一大革新之时代也。虽然,法律者,非创造的而发达的也。固不可不采人之长以补我之短,又不可不深察吾国民之心理,而惟适是求。故自今以往,我国不采法治主义则已,不从事于立法事业则已,苟采焉而从事焉,则吾先民所已发明之法理,其必有研究之价值,无可疑也。故不揣梼昧,述其研究所粗得者,以著于篇。语不云乎,层冰为积水所成,大辂自椎轮以出。此区区数章,苟能为椎轮积水之用,则吾之荣幸,宁有加焉?
一 法之起因
我国言法制之所由起,大率谓应于社会之需要而不容已,此儒墨法三家之所同也,今刺取其学说而比较之。
(一)儒家
《荀子·礼论篇》:人生而有欲,欲而不得,则不能无求。求而无度量分界,则不能不争。争则乱,乱则穷。先王恶其乱也,故制礼义以分之。以养人之欲,给人之求,使欲必不穷乎物,物必不屈于欲,两者相持而长,是礼之起也,故礼者,养也。
(又)《王制篇》:水火有气而无生,草木有生而无知,禽兽有知而无义,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,故最为天下贵也。力不若牛,走不若马,而牛马为用。何也?曰:人能群,彼不能群故也。人何以能群?曰:分。分何以能行?曰:义。故义以分则和(杨注:言分义相须也),和则一,一则多力,多力则强,强则胜物。……故人生不能无群,群而无分则争,争则乱,乱则离,离则弱,弱则不能胜物。君者,善群者也。
(又)《富国篇》:人伦并处(杨注:伦,类也),同求而异道,同欲而异知。生也,皆有可也。知愚同,所可异也。知愚分(杨注:可者遂其意之谓也),势同而知异。行私而无祸,纵欲而不穷,则民心奋而不可说也。如是则知者未得治也。知者未得治,则功名未成也。功名未成,则群众未县也(案:县同悬,谓悬隔也)。群众未县,则君臣未立也。无君以制臣,无上以制下,天下害生纵欲,欲恶同物,欲多而物寡,寡则必争矣。……离居不相待则穷,群而无分则争。穷者患也,争者祸也。救患除祸,则莫若明分使群矣。
(二)墨家
《墨子·尚同篇上》:古者民始生,未有刑政之时,盖其语,人异义。是以一人则一义,二人则二义,十人则十义。其人兹众,其所谓义者亦兹众(案兹同滋,益也)。是以人是其义以非人之义,故交相非也。是以内者父子兄弟作怨恶,离散不能相和合。天下之百姓,皆以水火毒药相亏害,至有余力不能以相劳,腐朽余财,不以相分,隐匿良道,不以相教。天下之乱,若禽兽然。夫明乎天下之所以乱者,生于无政长,是故选天下之贤可者,立以为天子。……天子惟能壹同天下之义,是以天下治也。
按:荀子之所谓礼所谓义,墨子之所谓义,其实皆法也。盖荀子言礼而与度量分界相丽,言义而与分相丽。墨子言义而与刑政相丽,度量分界也,刑政也,皆法之作用也。
(三)法家
《管子·君臣篇下》: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别,未有夫妇妃匹之合,兽处群居,以力相征。于是智者诈愚,强者凌弱,老幼孤独,不得其所。故智者假众力以禁强虐而暴人止,为民兴利除害,正民之德而民师之。……名物处违是非之分,则赏罚行矣,上下设,民生体,而国都立矣。是故国之所以为国者,民体以为国。君之所以为君者,赏罚以为君。
《商君书·君臣篇》: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时,民乱而不治,是以圣人列贵贱,制节爵秩,立名号,以别君臣上下之义。地广民众万物多,故分五官而守之。民众而奸邪生,故立法制为度量以禁之。
又《开塞篇》:天地设而民生之。当此之时也,民知其母而不知其父,其道亲亲而爱私。亲亲则别,爱私则险。民生众,而以别险为务,则有乱。当此之时,民务胜而力征,务胜则争,力征则讼。讼而无正,则莫得其性也。故贤者立中正,设无私,而民说仁。当此时也,亲亲废上贤立矣。凡仁者以爱利为道,而贤者以相出为务。民众而无制,久而相出为道则有乱,故圣人承之,作为土地货财男女之分。分定而无制,不可,故立禁。禁立而莫之司,不可,故立官。官设而莫之一,不可,故立君。既立其君,则上贤废而贵贵立矣。
《韩非子·五蠹篇》:古者丈夫不耕,草木之实足食也;妇女不织,禽兽之皮足衣也。不事力而养足,人民少而财有余,故民不争。是以厚赏不行,重罚不用,而民自治。今人有五子不为多,子又有五子,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。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,事力劳而供养薄,故民争。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。
以上三家五子之说,皆以人类之有欲为前提。谓生存竞争,为社会自然之现象,而法制则以人为裁抑自然,从而调和之。而荀墨商三家,谓人始为群,即待法治。韩则谓地广人稀时,无取于法,法必缘民众而需要始亟。是其微相异者也。韩子殆只认形成国家后之强制组织,而不认社会的制裁力,是其缺点也。盖韩子之学,渊源于老子。而老子谓郅治之极,无法而能治也(韩子谓人民少而财有余,故民不争。然人民少之时,财亦决非能有余。此可以生计学理说明之也。故韩子此前提实不正确)。人类有欲之一前提,亦老子所承认也。然其所以解决此问题之方法,则与诸家异。儒墨法诸家,皆以节欲为手段,故礼也义也法也,从此生焉。老子则以绝欲为手段。欲苟绝,则一切皆成疣赘矣。故其言曰,不见可欲,使民心不乱。又曰,常使民无知无欲,故无为而无不治。又曰,少私寡欲。又曰,不欲以静,天下将自定。皆其义也。虽然,人类之欲,果可得绝乎?不可得绝,则老子之说不售也。以今语说之,则生存竞争者,果为人类社会所得逃之公例乎?不可逃,则法制之起,其决不容已也。
荀子,社会学之巨擘也。其示人类在众生界之位置,先别有生物于无生物,次别有知物于无知物,次别有理性物与无理性物。谓人类者,其外延最狭,而其内包最广,与欧西学者之分类正同。彼之所谓理性,荀子所谓义也,亦谓之普通性,亦谓之大我(附注:义从我,从羊,会意字也。董子云:义者我也。其从羊者,所以别于小我。羊能群者也。故我国文字凡形容社会之良性质者,皆从之。“群”“善”“美”“义”等是也。考工记注曰:羊,善也。义从我从羊,所以示我之结集体,即所谓大我也)。此大我之普通性,即人类所以能结为团体之原因也(小野冢博士言:国家所由起,根于人类之普通性。而笕博士言:国家社会之最高原因,根于自我之自由活动。其所谓自我者,谓人类共通之大我也。与佛学之华严、性海相合。他日更详细介绍之)。荀子以义为能群之本原,洵批隙导窾之论矣。其《富国篇》所论,由经济的(生计的)现象,进而说明法制的现象,尤为博深切明。谓离居不相待则穷,故经济的社会,为社会之成始。谓群而无分则争,故国家的社会,为社会之成终。其言争之所由起,谓欲恶同物,欲多而物寡。欲者,经济学所谓欲望(德语之Begierde,英语之Desire)。欲多而物寡,即所谓欠乏之感觉(德语之Empfindungdes Mangels)。而欠乏之感觉,由于欲恶同物,人类欲望之目的物,如衣食住等,大略相同故也。荀子此论,实可为经济学、社会学、国家学等之共同根本观念也。
诸家之说,皆谓法制者由先圣先王之救济社会之一目的而创造之。语其实际,则此创造法制之人,即形成国家时最初之首长也。而此首长,以何因缘而得有为首长之资格?诸家所论,微有不同。墨子言选天下之贤可者,立以为天子。是谓最初之首长,由选举而来。然法制未立以前,何从得正确之选举,是不免空华之理想也。儒家皆言天生民而立之君,又曰亶聪明作元后。是谓由天所命,然兹义茫漠,不足以为事实也。荀子亦儒家,而所言稍趋于实,谓必功名成然后群众悬,必知者得治然后功名成。盖当社会之结合稍进,则对内对外之事件日赜。其间必藉有智术者或有膂力者,内之以维持社会之秩序,外之以保障社会之安宁,于是全社会之人德之,而其功名成焉,浸假其人及其辅翼者,遂独占优势于社会,此君主贵族所由起也。故曰群众悬而君臣立矣。
管子言智者假众力以禁强暴,其说明社会形成国家之现象,尤为盛水不漏。夫虽有智者,苟非假众力而国无由成。盖国家为人类心理之集合体。苟其人民无欲建国之动机,则国终不可得建也。而又非如民约论者流,谓国纯由民众建也。虽有众力,苟无假之以行最高权者,则国亦无由成。两相待而国立焉,制定焉。管子此语,今世欧西鸿哲论国家起原者,无以易之也。
又管子所谓“上下设民生体”。所谓“民体以为国”,实“最古之团体说”也(房注谓:上下既设,则生贵贱之礼,贵贱成礼方乃为国。以礼释体,实曲解也。民礼以为国,岂复成文义耶?管子又云:先王善与民为一类,与民为一体。则是以国守国,以兵守民也。君臣篇上正可与此文相发明。故管子实国家团体说之祖也)。盖上之对下,即全部对一部之意也,即拓都对么匿之意也。上下既设而肢官各守其机能,如一体然,而此人民结集之一体,则谓之国家也。商君《开塞篇》之论,言国家发生成长之次第,尤为博深切明:盖由家族进为社会,由社会进为国家;由爱治进为礼治,由礼治进为法治。其所经过之阶级,实应如是也。其所论亲亲、上贤、贵贵之三时代,亦与历史相吻合。其上贤之一时代,即由图腾社会形成国家之过渡也。而所谓贤者,谓智力优秀于其俦者也。盖虽在未成国家以前,而社会上优秀者之地位已渐显,即所谓上贤时代也。及优秀者之地位被确认,则所谓贵贵时代也。
商君言制之兴,在未立君以前。夫在原始社会,其未立君者,即其未形成国家者也。谓未形成国家而先有法制,似不衷于理论。虽然,未有国家以前,夫既有社会之制裁力,商君所谓制者,盖指此也。故别前者谓之制,而后者谓之禁。制者相互的,而禁者命令的也。故禁也者,即国家之强制组织也。而禁之与官,官之与君,同时并起,非谓先有禁而后有官,先有官而后有君,精读原文,自不至以辞害意焉矣。
小野冢博士者,日本第一流之学者也,今引其言以证管、商二子之说。其言曰:“原人最始为徽章(图腾)社会。而此种社会,由家庭团体时期,渐进于地域团体时期……当其未形成国家以前,亦固思所以调和冲突,维护内部之平和。其间自有规律之发生,略约束其分子。但此规律,无组织的强制力之后援,苦失诸微弱。洎夫内部之膨胀日增,对外之竞争日剧,于是社会之组织,分科变更,而强制的法规起焉。强制法规既具,不可无统一之机关。群中之优秀者,则膺其任而执行之。始犹不过暂置,既而内外之形势继续,而机关遂不得不继续,而所谓优秀者,遂得继续以保其优势之地位。故原始国家与君主国体,常有密接之关系,非偶然也。”(《政治学大纲》上卷第一四五至一五○页)此与商君之言,抑何相类之甚耶?而其所谓优秀者,亦即管子所谓假众力以禁强暴之智者也。荀墨两家,仅言礼言义言分,是所重者,仍在社会之制裁力也,混道德与法律为一也,所谓礼治主义德治主义也。管商皆言禁,则含有强制组织之意义,而法治主义之形乃具矣。此法家之所以独能以法名其家也。
《汉书·刑法志》:夫人宵天地之(颜注云:宵,义与肖同。,古貌字),怀五常之性,聪明精粹,有生之最灵者也。爪牙不足以供耆欲,趋走不足以避利害,无毛羽以御寒暑,必将役物以为养,任智而不恃力,此其所以为贵也。故不仁爱则不能群,不能群则不胜物,不胜物则养不足。群而不足,争心将作。上圣卓然先行敬让博爱之德者,众心说而从之。从之成群,是为君矣。归而往之,是为王矣。洪范曰: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。圣人取类正名,而谓君为父母。明仁爱德让,王道之本也。爱待敬而不敝,德须威而久立,故制礼以崇敬,作刑以明威也。圣人既躬明哲之性,必通天地之心,制礼作教,立法设刑,动缘民情,而则天象地。
此文言法制起原,兼采儒墨法诸家之说而贯通之,明社会制裁力,与国家强制组织,本为一物。礼治与法治,异用而同体,异流而同源,且相须为用,莫可偏废。此诚深明体要之言也。读此,而我国人关于法之起因之观念,可以大明。
二 法字之语源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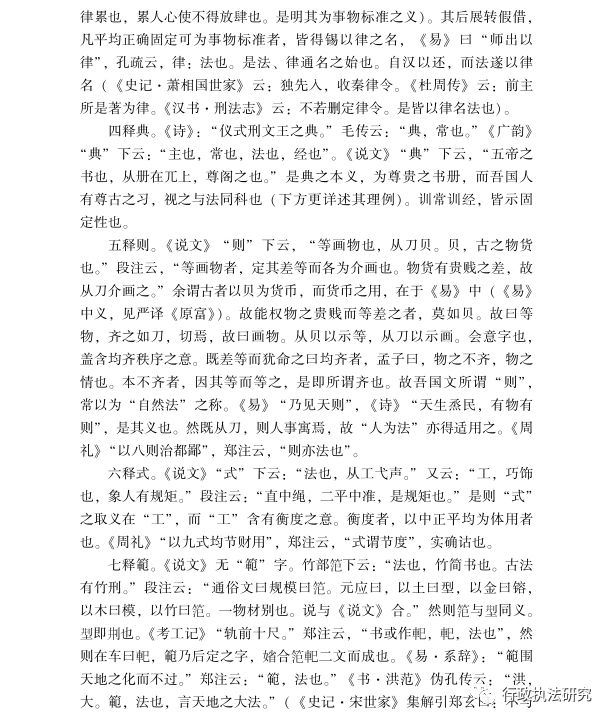

三 旧学派关于法之观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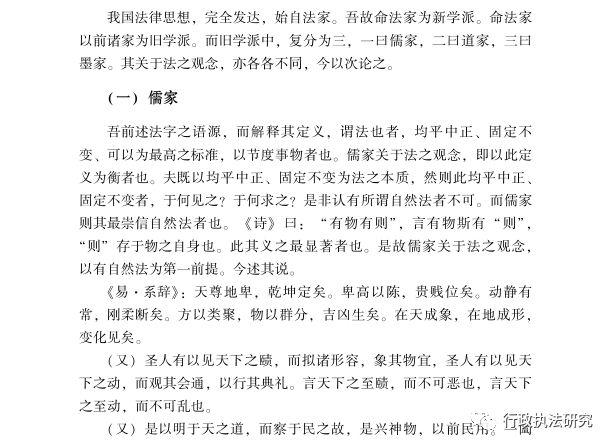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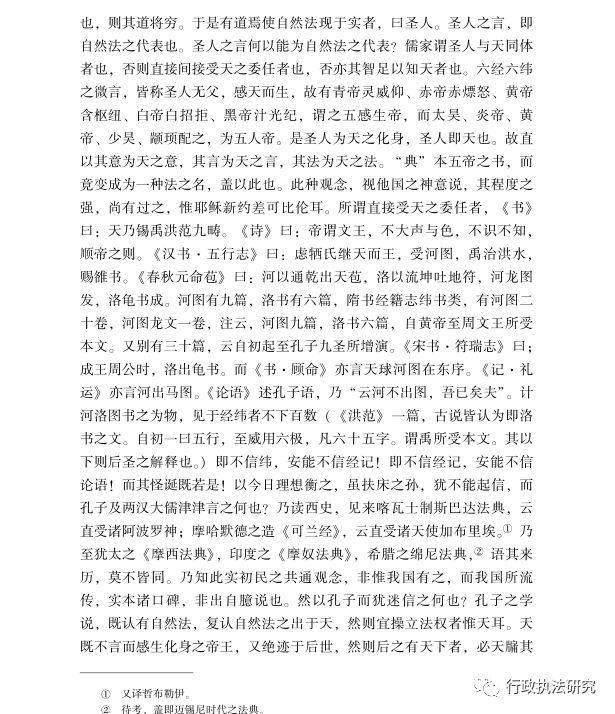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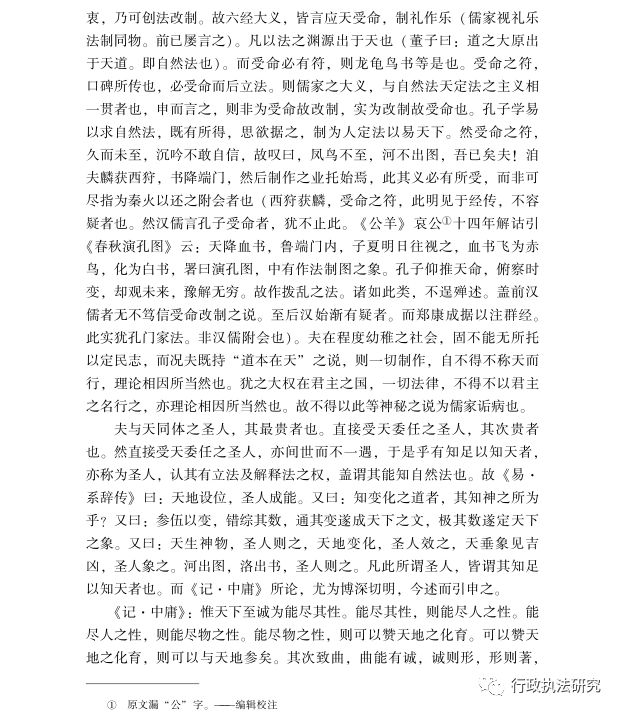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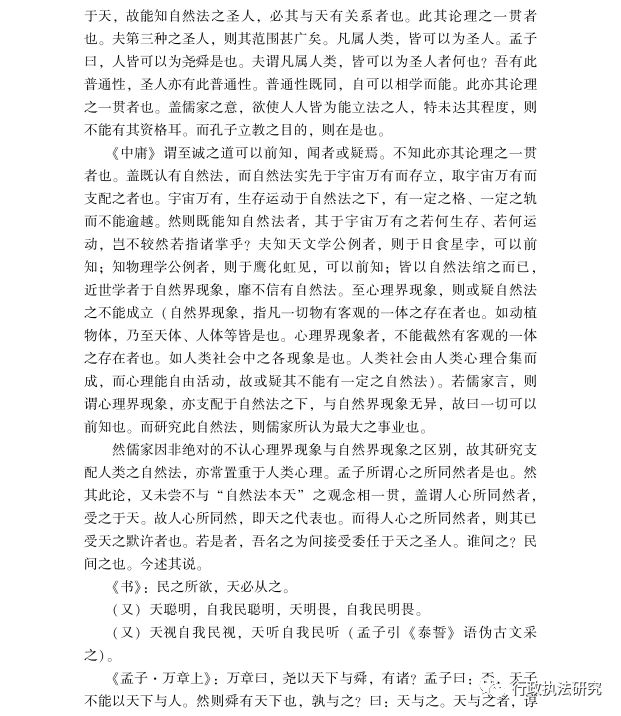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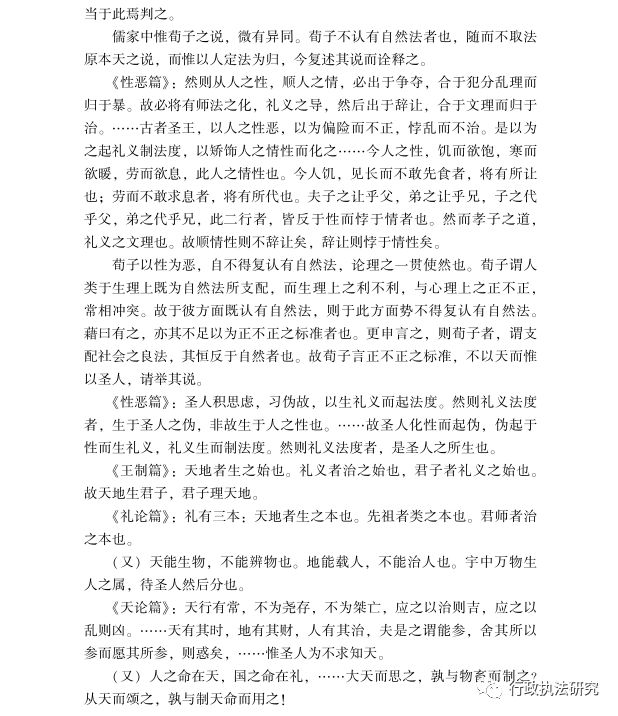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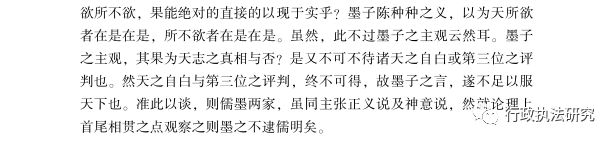
四 法治主义之发生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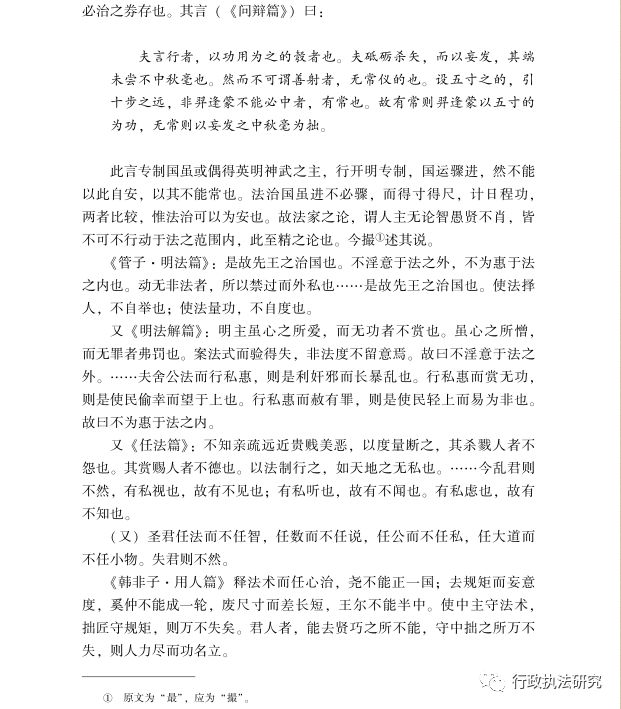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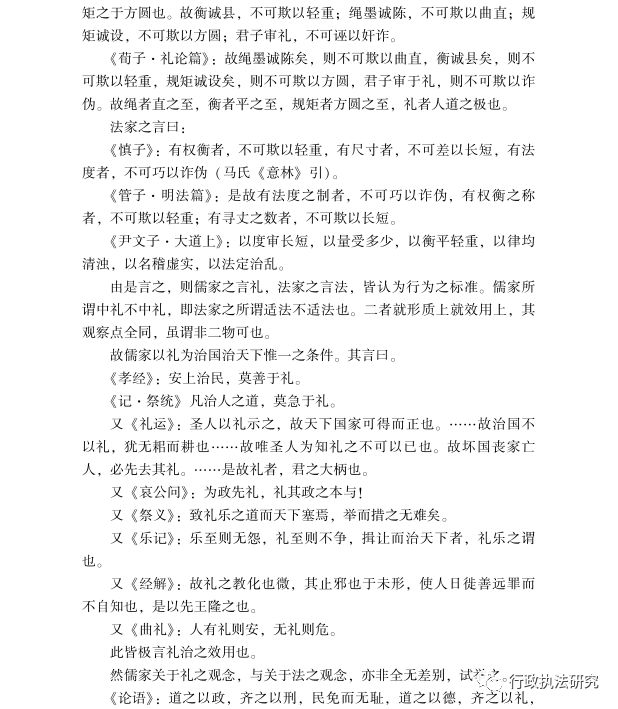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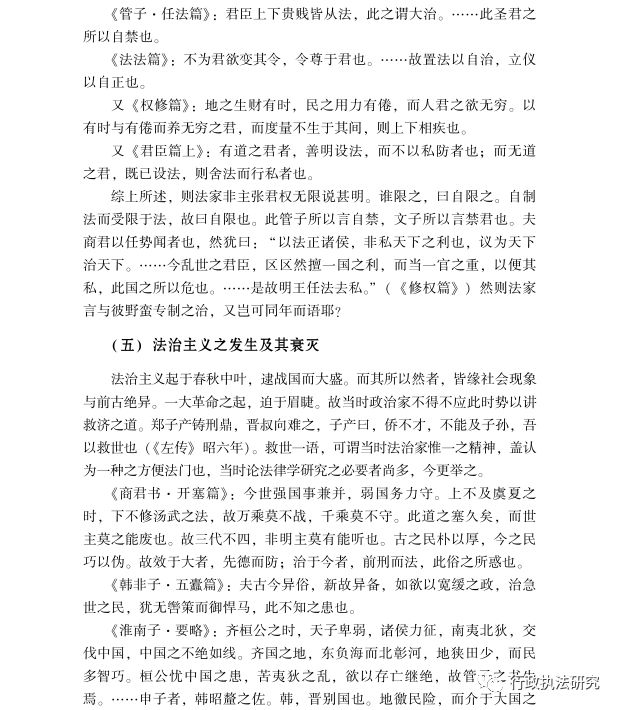



文章来源:《法律文化研究》 2014年00期。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
责任编辑: